想像天使在流水线上生产雪花
家乡区县: 湖北省红安县
包装车间灯火通明
我手握电熨斗
集聚我所有的手温
我要先把吊带熨平
挂在你肩上才不会勒疼你
然后从腰身开始熨起
多么可爱的腰身
可以安放一只白净的手
林荫道上
轻抚一种安静的爱情
最后把裙裾展开
我要把每个皱褶的宽度熨得都相等
让你在湖边
或者在草坪上
等待风吹
你也可以奔跑
但,一定要让裙裾飘起来
带着弧度
像花儿一样
我要洗一件汗湿的厂服
我已把它折叠好
打了包装
吊带裙
它将被打包运出车间
走向某个市场
某个时尚的店面
等待惟一的你
陌生的姑娘
我爱你
——邬霞《吊带裙》
写《吊带裙》的时候,邬霞已在深圳工作了12年。1996年,作为第一代留守儿童,14岁的邬霞从四川内江千里迢迢来到父母打工的深圳,进入了母亲工作的制衣厂,成为一名童工。
从此,邬霞再没回过四川老家。真正意义上地扎根深圳是她这20年来最大的梦想。青春就像线头被岁月的剪刀一刀刀剪掉。但在深圳打拼二十年,带着两个孩子的她和父母、妹妹6口人依旧挤在破旧逼仄的出租屋里。
邬霞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说,初入社会的自己也有过自杀的念头。在一次被工厂的管理人员训斥后,邬霞冲到公共洗澡间,推开窗户。把脚伸出去的一刹那,邬霞觉得好轻松,感觉跳下去就没有烦恼了。
比许立志幸运的是,跟她在同一家工厂打工的母亲赶上来一把拉住了她。母亲哭着对她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只要活着,就一定有希望。”
后来,写作成了伴随邬霞打工岁月的精神支柱和希望。还住集体宿舍的时候,晚上十一二点下班,吃个宵夜,排队洗衣服洗澡。完成这些后,邬霞就爬到上铺,拉上帘子,一页页地编织着自己的精神世界,直到凌晨三四点。
邬霞笔下的女孩们往往过得都比她好。就如这首《吊带裙》,读不出大多数打工诗歌的惨烈和压抑。这也是她被秦晓宇和吴飞跃看重的地方。在纪录片《我的诗篇》里,邬霞被选中成为六名主要角色之一。
摄制组去邬霞家里拍摄,邬霞和妹妹问导演吴飞跃,能不能帮她们录制一些唱歌的视频。原来,在诗歌中给予女孩阳光和幸福的邬霞,这几年的生活愈发艰难。
身患重病的父亲因为抑郁,几次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虽然在父亲被抢救时,文友们的爱心捐赠帮助邬霞一家渡过难关。但父亲的病没有好转。她告诉吴飞跃,自己和妹妹想去《中国梦想秀》碰碰运气。在朗诵会上播放的纪录电影的预告片中,邬霞说,即便再重的石头压着我,我也要昂着头,等待那束阳光。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就送梧桐子“ ”支持吧!
”支持吧!
已获得0个“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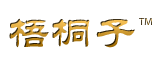
 河南省孟州市
河南省孟州市 山东省新泰市
山东省新泰市 广州市海珠区
广州市海珠区 安阳市 北关区
安阳市 北关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