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明题&小妖UU(上)
家乡区县: 重庆渝中区
最初,我们无法证明一切。后来,有人证明了地球是圆的,再后来,有人证明了人是由猿猴进化来的,再再后来,我们证明了越来越的东西,却发现需要证明的东西同样变得越来越多。最后,证明成为一道题目,出现在所有人的数学课本中,甚至就连我们的生命,也是从一份出生证明开始,以一份死亡证明终结。
这时,我们才发现,当一切无法证明的时候,才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候。
1.
第一次见到戴宇是在湖边。他当时淹没在人群里,举着手里的布偶,摆着不情愿的笑向游人推销那做工粗劣的布偶。
那天是五月的一个周末,北方的春天犹抱琵琶半遮面,虽然春暖,但尚未花开。小城公园中的人造湖里,荡漾着微寒的春光,湖边立着一个纪念碑,碑上刻着一个英武的男人在湖水中奋力直游,那是建湖初始,一个为了救落水者而牺牲的英雄。从那一年开始,这湖每年都要淹死个把人,今年特别。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往年淹死的都是不幸落水者,今年淹死的都是殉情自杀的。
人们发现的第一具尸体是一个女人。那时正是三月初,冰雪刚刚融化,公园的管理员准备清理下湖面,迎接春天的第一批游客,他刚刚敲开边缘的那层薄冰,女人的尸体就如气球一般浮了上来。她或许是初冬正在结冰的时候死的,也或许是冬天凿开冰面钻进水里的,总之她死了很久了,身体肿胀得如她左手腕纠缠着的布偶一般。人们就是通过那个布偶判定她是殉情自杀的,她的左手和布偶的右手用一根红线紧紧绑在一起,布偶的胸前隐约写着一个名字,但泡了太久,已经无法辨认了。她定是得不到他,才会用布偶代替他共赴黄泉。
公园女尸的新闻震撼了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他们用自己的方式理解了她的死,并在这种理解中感动了自己。更有些和她同样境遇的女人、或者男人,从她的死亡里获得了某种凄婉惨烈的启发,于是,第二具浮尸出现了,继而是第三具、第四具……他或她的手臂上,都用红线缠着一个男布偶或女布偶,虽然样子各异,却无一例外的写着某个人的名字。再后来,受到的启发的人又将死亡方式升级——那些深深相爱着,却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在一起的恋人,用红线将彼此的手臂缠绕在一起跃进湖中,以此证明他们生死相许的决心。
然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座一直吞噬着生命的湖,并没有因为今年胃口大开而让游人蒙上阴影、望之却步。相反,来这里游湖的人比往年更多了,且都是一对一对的,看得令人心惊,总担心他们随时会成为下一对殉情者。
我的噩梦就是从这座湖开始的,或许,是从看到戴宇的那一刻开始的。
2.
我知道宋琦最怕什么,每当我在他的怀里摆出提问的表情时,他的眼睛里就会闪过一丝慌乱,就像课堂上那些不知道答案的学生一样,一遇到老师提问就会神情恍惚。
宋琦越是如此,我越是要问他,因为对于这个问题,他不该慌乱、不该恍惚、不该不知道答案的——那个问题是:你爱我吗?你确定你爱我吗?
我知道他每次肯定都会回答:“爱”。但我不知道他给出的这个答案是真命题还是假命题,我需要证明:一件绝版的时装或者一枚新款的首饰,哪怕是一张难吃的外国馅饼或者一枚别致的纽扣都能证明他的爱,虽然我并不喜欢它们,但它们能让我对他的爱感到安心。
我不贪财,我贪爱。
在遇到戴宇的前一天晚上,我牵着宋琦的手,含情脉脉:“你爱我吗?”宋琦不知道我又要什么,有些虚虚地答:“爱。”
“那我们趁着明天是周末去游湖吧!你知道的,等周一到新学校报到后,我就要忙起来了。”我指着电视,里面正在播本地新闻,又一对殉情者的尸体被打捞上来,他们被水浸泡过的皮肤皱在一起,男人的左手和女人的右手被一条红线紧紧捆着,刺眼的红。我想,殉情者的灵魂赋予了湖爱情的魔力,只有在那座湖上,才能证明彼此的爱。
宋琦誓死不去,他觉得那湖很邪门。这是他第一次如此决然地拒绝我,我泪眼婆娑地问:“你难道不爱我吗?如果有一天我让你和我一起去死,你愿意吗?”
宋琦心中积压了很久的不满终于爆发出来:“我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去死?!我不会为任何人放弃我自己的生命!”
你看,他连敷衍一下都不肯了,他不爱我了。那晚,我们一直吵到半夜,吵架的内容就是爱:爱吗?爱!那怎么证明你爱?不需要证明!不证明就是不爱!好吧,不爱!既然不爱就分手吧!行!这是你说的!分手吧!好!分就分!那,你给我滚!滚就滚!
第二天,我挂着黑眼圈一脸憔悴地独自去了那座公园、那座湖。可惜,在一系列自杀事件之后,公园暂时禁止了游湖,湖边小码头上那些造型各异的小船都被铁链子锁了起来。岸边有个少年在卖情侣布偶,臃肿的西装牵着臃肿的婚纱,它们的左手和右手被一条鲜红的丝线捆着,仿若刚刚打捞上来的尸体。不少望湖兴叹的情侣买了布偶,在它们背后写上各自的名字,抛进湖里,于是它们成了真的浮尸,代替他们。
看到这一幕,我不由扬起嘴角。现在的孩子真是越来越有经济头脑了,小小年纪就懂得抓住商机投机赚钱。
这时,一个抱着布偶的小女孩突然走到我身边,指着那少年,怯怯地问:“你是在对他笑吗?”她说着,抬起头,那一刻,我怀疑自己出现了幻觉,尖叫着跌坐在地上。
女孩脖子两侧青色的血管在她苍白的皮肤下微微凸出,一道暗红色的刀疤结着丑陋的痂,像一道抛物线,将A血管和B血管紧紧连在一起;她抬起胳膊指着少年时,衣服的宽袖垂下来,她右手的手腕上绑着一根耀眼的红绳,红绳下面,印着两道同样鲜艳的平行线。
少年循声跑来,抱起小女孩,充满敌意地望着我,那种阴冷的眼神,我只有在《动物世界》才见到过。
3.
知道他叫戴宇,是在第二天上课的时候。
那天我打了很厚的粉底,尽量让自己显得光鲜照人。我一走进教室,班里的男生们就发出一阵惊叹,继而在班长的一声“起立”后,孩子们参差不齐地站了起来,我一眼就看到了他站在最后一排,面无表情、目光里什么也没有,就像布偶脸上用来点缀的玻璃珠。
我循着贴在讲桌上的座位表找到他的名字,戴宇,我记得。
为了在最短的时间适应新的学校、了解自己所带班级的数学成绩,我连夜翻阅了孩子们作业本,其中最破的一本是戴宇的,里面红叉叉最多的也是戴宇。他的代数作业完成的都很好,唯有几何证明题没有一道正确的,让他证明“A”,他得出的永远是“B”,或者“C”,或者干脆一片空白。那时我就决定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学生,我喜欢挑战这样的孩子,在我的字典里,除非天生智障,否则没有我教不会的。
我捻了捻手上的的粉笔头,在黑板上写下了:“在正方体ABCD-A'B'C'D'中,M,N,P分别是CC',B'C',D'C'的中点,求证:AP垂直于MN”。那个“N”字拉了一条长长的线,粉笔头的生命在那道长线中终结。我蹭了蹭手指上白色粉末,假意环顾了一下教室,然后将目光落在戴宇脸上。直到这时,他的眼睛里才有一丝正常人该有的表情——慌乱,就像宋琦在说爱我的时候一样。
“戴宇。”我微笑着:“你上来做一下这道题。”我想通过这种方式刺激他理解证明题正确思路,参悟到证明题的真谛。其实那些证明题,无非是费尽周折,去证明一个已经知道的答案而已——真命题,或假命题。
戴宇低着头,冷冷地:“我不会。”
我继续保持着微笑:“没关系,我可以教到你会为止。”
他慢腾腾地站起来,茫然的目光穿透我的身体,落在黑板上,就这样愣了一小会儿,才晃荡着肥大的校服,低着头挪向讲台,每一步里都塞满了“不情愿”,仿若讲台就是断头台,而我就是站在铡刀旁的刽子手。
他用粉笔一般的手指从讲桌上的纸盒子里抽出一根手指一样粉笔,恨恨地看了我一眼,然后紧紧咬着嘴唇,在黑板上画了一个立方体,那立方体似乎也感染了他的情绪,每一条线都虚弱地颤抖着。
他在题目下面写下“解答:(1)∵”,便低下头,双手折磨着粉笔,一小截一小截地掰下来,攥在手心里,又碾成粉末。
我轻轻在立方体上画了一道虚线:“你必须首先证明……”
“你能证明吗?”他突然扭过头,低低地说。那一刻,他的脸又恢复原来的样子,苍白、瘦削、冷漠,看得人彻骨的凉。
“证明什么?”
他不屑地笑笑,将嘴附在我的耳边:“证明我杀过人。”说罢,他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教室。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就送梧桐子“ ”支持吧!
”支持吧!
已获得0个“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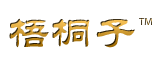
 河南省孟州市
河南省孟州市 山东省新泰市
山东省新泰市 广州市海珠区
广州市海珠区 安阳市 北关区
安阳市 北关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