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世界 影评:卡在梦想与现实之间的世界 7
家乡区县: 宜春市袁州区
赵涛与赵小桃
《世界》的剧本是根据赵涛在深圳世界之窗当舞蹈演员时的经历改编的。改编出来的故事保留了几分真观众不知道,掺了几分假倒是很容易看出来。
城市由深圳改成了非常概念化的北京。《世界》中的人物与他们所在的北京没有任何交流和互动。故事放在北京却没有任何北京的痕迹。那么把地点改成北京的意义何在?我很业余地揣测,贾樟柯本人在北京生活过多年,却没在深圳生活过,所以地点在北京本能地让贾樟柯感觉更踏实。另外,北京故事显然比深圳故事更能吸引眼球。可是这样一来,赵涛亲身经历中的城市场景,那个城市给她的真实的印象和她对那个城市的个人感情,势必不可能被简单转换到北京。不信?你能想象把《小武》的背景放到湖南吗?所以在贾导演烹制的《世界》里,观众看不到北京给小桃的印象,也看不到小桃对北京的感情。《世界》是个孤零零悬浮在宇宙中的世界,北京在《世界》里是个概念化的北京。
更让人觉得导演思维混乱的是,位于深圳华侨城的印有世界地图的几座标志性建筑在《世界》的片头反复出现。其荒谬无异于在一个背景在纽约的电影中穿插金门大桥的镜头。
赵涛说过自己刚到深圳时感觉一切都很新鲜,常和小姐妹们逛街等等。这些亮色都被过滤掉了,《世界》里的赵小桃从头到尾都很郁闷。事实是赵涛本人后来回山西当舞蹈教师了;事实是我私人认识的一个曾在世界之窗当舞蹈演员的女孩后来当电视台节目主持人了。而《世界》里的舞蹈演员都是什么出路呢?有傍大款的,有自焚的,有当妓女的,有煤气中毒的,有靠和领导睡觉升官的,就是没有正常的。升官的那位陪领导睡觉的戏被剪掉了,因为贾樟柯自己觉得“编得不好”。我完全同意。
我不反对揭露残酷的现实。正相反,我并不赞同像张艺谋那样为了增加亮色而把《活着》里的两个死人拍活。我的观点是,亮色和阴影本来就真实地并存着。眼神儿不好使的导演才总觉得有需要人为地抹黑、增加亮色、或者剔除亮色。在《世界》里你看不到学跳舞时露出腼腆笑容的、在澡堂里放声歌唱的小武,看不到踏着“成吉思汗”的节奏脚步轻快的张军,追火车的崔明亮,刚烫了头的钟萍,和在办公室里闻歌起舞的尹瑞娟,也看不到那个说“它自己飞过来停到这儿”的巧巧。《世界》满目疮痍,如履薄冰。难怪苏童要激动地说《世界》是贾樟柯最大胆、最尖锐的一次。可导演、作者的大胆、尖锐程度与电影、小说的好坏有必然联系么?一堆土豆里捡最难看的拍和捡最漂亮的拍有什么本质区别么?这也罢了,要是导演还嫌弃这个最难看的土豆不够难看,还要给它脸上擦点泥巴,非其最痛苦最脆弱的一面不拍,就有点儿过了。
幸而贾樟柯说他自己也还是最喜欢《站台》。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就送梧桐子“ ”支持吧!
”支持吧!
已获得0个“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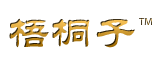
 河南省孟州市
河南省孟州市 山东省新泰市
山东省新泰市 广州市海珠区
广州市海珠区 安阳市 北关区
安阳市 北关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