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名字叫做尘
家乡区县: 湖南省安化县
灰白色的天空,像裹上的一件纯棉休闲外套。干净挺括,线条分明。 天空上游移的云层,它们带着庞大的水汽,想一个来自远方的悲伤的诗人,把蘸满水墨的笔,轻轻地点在宣纸上,均匀地晕染开来。风摩挲着水沙褪掉叶子的躯干,以灰白色的天空作为背景,像十八世纪中期的一幅油画。 这幅画离我有多远?一秒?一天?还是几千几万年的浩渺?我伸出手在光影中抚摸,近在咫尺,又隔天涯。 我从未想过,我梦境中那些猛烈地风,天地间茫茫的雪花,鸟群的悲鸣穿过凝滞的时空,在割裂的年轮里,粗重而缓缓的转轴中,蒸发成灰烬。有关于江南氤氲的水汽,被雨打湿的倒影,如锦缎的年华。 你在无尽的荒凉中,手持一朵莲花。 每天早晨,三月低冷的空气总是侵入我的每一个毛细孔,我的衣服并不多,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打着哈欠,反复摩擦手臂告诉自己,太阳很快就出来了。但我等来的光在寒冷的空气中透明而不温暖。我总觉得自己的衣服太少了不够穿可周末却接二连三地掏光钱买一件件普通的白色棉质春装。 高三的生活,忙而乱,我在白天与黑夜的间隙没顾得上整理自己的房间,我也没心情去整,每天心绪烦躁地关掉聒噪的闹钟,在床上赖几分钟起来迅猛地洗脸漱口,抓起单肩包飞奔出去,在过马路时,灰暗的早晨中明灭的车灯从远处投过来,照得我手足无措。 像被光明刺穿得千疮百孔的深浓雾气。 这个季节又从各座城市回来的朋友,怀揣着他们的艺术梦想,或者是被告知谁选择了传媒,谁的生日蛋糕里幻想着一张中央美院的录取通知书,他们的表情在晴光下在阴天下,在灯光里在黑夜的烛光中温柔安静,他们眼神中多了一丝我看不透的东西,他们带着天南地北的普通话口音,恬静深沉的笑容,棕色的夹克卫衣,双肩包、画板,或者经过舞蹈培训过的独特气场。一切的一切,在我发现周围的氧气越来越稀薄时,暗暗自惊各奔前程是一句很容易的话,说着说着就成了真。 而那些无端的伤感成了这个忽冷忽热的季节里最可笑也最不值钱的东西。 至于我为什么伤感不起来,大概早被时间掠去了轻浮的外表,和漫长的消耗后,留下了粗砥的内核。 我想到了那个在深夜里敲字敲到手臂发酸的男孩。 他的东西不需要得到这个世界的认可,被嗤之以鼻或者奉为圭臬都是无关痛痒之事,多了只会让人更迷失自己。可有一天,他不敲字了,他每晚喝一杯一杯的咖啡,窗外深浓的夜色令人窒息,在黑暗中打开台灯拿笔在稿纸上飞快地演算,密密麻麻的日子铺满了每一处缝隙,他看到镜子里凹陷的眼球疲倦的肤色,呆了几秒。第二天早晨因为胃很难受趴在厕所里吐得一片狼藉。食道里有一只手抓住了咽喉一样发不出声音,他依旧清理好自己的衣服,带好厚厚的复习资料出门。 这就是他的生活。他默默告诉自己,无可厚非,惟愿生活与理想皆无恙。 世界上永远都有一种道路,像希望一样可有可无,你可能奔跑在被划破的气流里,像韩寒那样用七门功课的红灯,指引了自己的前进。可能摇晃在钢丝绳上,一部分人未足先登,另一部分人一不小心便溺死在平庸的海洋中。 他的刘海遮住了右眼,说:看来,你人生的经历甚至比我还狭窄。 他的衬衫飞扬在上海的风中:但,这是我理想的生活。 他们都属于极端。很多人以为很多人都是这样,直到现实卑微而坚定地站在面前说:他们遥远着呢,他们平凡着呢。 我只记得,我的生活中,曾出现过这些,但也很快消失。 “在黑色的风吹起的日子,在看到霰雪鸟悲鸣的日子,在红莲绽放樱花伤势的日子里,在你抬头低头的笑容间,在千年万年的罅隙中,我总是意犹未尽地想起你。这是最残酷也是最温柔地囚禁吗?” 别把他想得太重要了,他只是一颗尘埃。 Dark Willioms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就送梧桐子“ ”支持吧!
”支持吧!
已获得0个“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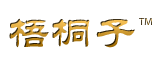
 河南省孟州市
河南省孟州市 山东省新泰市
山东省新泰市 广州市海珠区
广州市海珠区 安阳市 北关区
安阳市 北关区